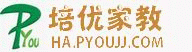《罗密欧与朱丽叶》
【背景知识】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共写有37部戏剧,154首14行诗,两首长诗和其他诗歌。其主要成就是戏剧,按时代、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发展,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
早期(1590—1600):这时期的伊丽莎白中央主权尚属巩固阶段,王室跟工商业者及新贵族的暂时联盟尚在发展,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国势大振。这使作者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相信人文主义思想可以实现。这时期所写的历史剧和喜剧都表现出明朗、乐观的风格。代表作有历史剧《理查三世》等,喜剧《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中期(1601—1608):这时英国农村的圈地运动正在加速进行,王权和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暂时联盟正在瓦解,社会矛盾深化,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詹姆士一世继位后的挥霍无度和倒行逆施,更使人民痛苦加剧,反抗迭起。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加剧,创作风格也从明快乐观变为阴郁悲愤,其所写的悲剧也不是重在歌颂人文主义理想,而是重在揭露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他写有7部悲剧,其中“四大悲剧”作于这个时期。《哈姆雷特》展现了一场进步势力与专治黑暗势力寡不敌众的惊心动魄的矛盾斗争。《奥赛罗》描写了一幕冲破封建束缚又陷入资本主义利己主义阴谋的青年男女的感人爱情悲剧。《李尔王》描写刚愎自用的封建君王在真诚和伪善的事实教育下变为一个现实而具同情心的“人”的过程。《麦克白》则揭露权势野心对人的毁灭性腐蚀毒害作用。
晚期(1609—1613):这时詹姆士一世王朝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退居故乡写浪漫主义传奇剧。
马克思称莎士比亚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恩格斯盛赞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莎氏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1919年后被介绍到中国,现已有中文的《莎士比亚全集》。
【阅读指导】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的一部爱情悲剧。它依据一个流传的意大利爱情故事加以改写,赋予它全新的内涵。全剧以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幸福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为线索,展开戏剧冲突,一方面谴责残酷的封建世仇,批判腐朽的封建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歌颂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寄托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渴求幸福,反对禁欲的人文主义理想。
这是一首青春和爱情的赞歌,全剧贯穿了爱和恨的斗争,美好的爱情理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悲剧主人公是一对热恋的青年,他们互相倾慕,忠于自己的爱情,忠于自己的誓言,但在当时的家族世仇和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阻碍下,最后只落得双双殉情的悲剧结局。
入选教科书的是原作第二幕第二场,这一场简称“阳台会”。它描写罗密欧在凯普莱特家花园里与朱丽叶幽会的情景。这场戏历来被公认为描写少男少女爱情的经典,广为传诵,以至后世人们习惯地将最美好的爱情称之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
这场戏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会面前的独白;二是两人对白;三是奶妈呼唤,两人分手。
第一层次(开头——“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两人独白,表达相思。
罗密欧在月夜“借着爱的轻翼飞进园墙”,站在朱丽叶的阳台下,仰望着意中人。他们这样相会,如朱丽叶所说,“太仓促,太轻率,太出人意外”,带有传奇色彩。罗密欧首先暗自赞美朱丽叶的容貌。这时还没有会面交谈,在激动中尚能保持冷静,所以罗密欧的大段诗句,从容而又欣喜地表现对朱丽叶的歌颂和爱慕,词句华丽,意象鲜明。莎士比亚以光明和黑暗来象征爱情和仇恨。当罗密欧在舞会上初次看见朱丽叶时,就说:“啊,火炬远不及她的明亮……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第一幕第五场)现在看到她在阳台上窗户中出现,又说:“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罗密欧以日月星辰来比喻朱丽叶的光华艳丽,他的想像深远而真切。他赞美她的眼睛是“天上两颗最灿烂的星”,形容她的面貌,“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看到她手托香腮,他说:“啊,但愿我是那一只手上的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当罗密欧幽然长叹时,他形容自己像一个尘世的凡人,“张大了出神的眼睛,瞻望着一个生着翅膀的天使,驾着白云缓缓地驰过了天空”,真实刻画出初恋时仰慕的心理。
朱丽叶最初还没有发现罗密欧在阳台下,她吐露内心秘密,语言朴素坦率,情意深切真挚。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但家族的世仇横亘其间。朱丽叶深爱罗密欧,面对家族世仇和心中挚爱的矛盾,她想到“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真心相爱,姓名可以抛弃不顾。她说:“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的完美也决不会有丝毫改变。”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家世代表着身份和地位,这对于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来说,尤为重要,但朱丽叶却弃之若屣,勇敢地迈出了叛逆的第一步,显示了爱情的力量。
第二层次(“你是什么人”——“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两人对白,说爱盟誓。
当朱丽叶发现罗密欧时,她问他怎样来到园中,告诉他到这里会有生命危险,但此时的罗密欧忘记了一切,他倚在窗下,向心爱的人倾诉衷肠:“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园墙,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阻隔的;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它都会冒险尝试,所以我不怕你家里人的干涉。”面对可能有的杀身之祸,他毫不畏惧:“只要你爱我,就让他们瞧见我吧;与其因为得不到你的爱情而在这世上挨命,还不如在仇人的刀剑下丧生。”
此时,朱丽叶抛弃了少女的羞怯和矜持,更抛开了束缚思想感情的“虚文俗礼”,大胆表达爱情,并要罗密欧起誓证明真心。当罗密欧要对月亮起誓时,朱丽叶又两次拒绝,她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在她眼里,上帝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万物(包括月亮)也是靠不住的,惟一值得信赖的是情人自身:“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会相信你的。”罗密欧的答话,显示出他已将爱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冒险跳进园中这一行动,就是爱情的明证,没必要再多说什么,所以在交谈中,朱丽叶的话比罗密欧的多。莎士比亚运用语言,总是联系人物性格和特定情境。一对情人初次交谈,内心激动,出言吐语,不加雕琢,风格简练自然。
第三层次(“幸福的,幸福的夜啊”——结尾):两人定情,不忍分别。
此时已是深夜,奶妈三次呼唤朱丽叶,她两次去而复返,并且喊回已经告别的罗密欧,决定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派人去找罗密欧商定结婚大事。这时他们更加激动,情感急切,台词的动作性多于抒情性。
分别之际,两颗心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奶妈频频呼唤,朱丽叶催促罗密欧离开,内心非常矛盾,情不自禁呼唤心爱的人的名字。罗密欧惊喜若狂:“那是我的灵魂在叫喊着我的名字。”可当他回转来时,朱丽叶却说:“我记不起为什么要叫你回来了。”朱丽叶舍不得罗密欧离去,又担心爱人死在自己的爱抚里:“天快要亮了;我希望你快去;可是我就好比一个淘气的女孩子,像放松一个囚犯似的让她心爱的鸟儿暂时跳出她的掌心,又用一根丝线把它拉了回来,爱的私心使她不愿意给它自由。”罗密欧狂喜地回答:“我但愿我是你的鸟儿。”处于情感高峰上的恋人都心甘情愿失去自我,把自己完全融进对方的身体和灵魂里去。这种融合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获得最大的自由。为此,朱丽叶甘愿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罗密欧:“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淼,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热恋中的情话常常是颠三倒四的,没有逻辑只有痴迷。
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细致写出爱情的高峰体验及其过程,这种高峰体验不仅寄寓着莎士比亚的爱情理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对人与人之间友爱和谐关系的追求。
节选这场戏十分注重气氛的渲染和营造,莎士比亚充分利用环境来烘托气氛,如神秘的夜色、静谧的花园、皎洁的月亮、温暖的晨曦;另一方面运用西方诗歌中适合于描写爱情的诗体,如十四行诗等,让两个恋人在诗情画意中唱出一首首美丽的抒情诗。如“美丽的太阳”一段抒情独白(“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好让我亲一亲她脸上的香泽”)中,莎士比亚综合运用比喻、拟人、象征、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一段段独白、对白充满诗意。他不仅把朱丽叶比喻为美丽的太阳,表达对她的赞美之情,还将月亮拟人化,比作有嫉妒心的人,因不如朱丽叶美丽,“已经气得面色惨白”。太阳象征着纯洁的爱情,而“妒忌的月亮”则象征着家族怨仇与世俗礼教,“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妒忌的月亮”,深层次地象征了坚贞纯洁的爱情,必将战胜家族怨仇与世俗礼教的美好愿望。“既然她这样妒忌着你,你不要忠于她吧;脱下她给你的这一身惨绿色的贞女的道服,它是只配给愚人穿的。”这里的“绿色贞女的道服”象征着封建包办婚姻,说“它是只配给愚人穿的”,表达了主人公对它的憎恶和反叛,也反映了对自由婚姻的憧憬。独白中还将朱丽叶的眼睛同天上的星星对比,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以突出朱丽叶的光彩照人。此外如“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园墙……”、“我给你的越多……”等脍炙人口的片段也都为人传诵不衰,成为抒情诗中的精品。